一个迷途的女人(一)
迷途
德拉诺什,我的兄弟。
我现在满脑子,满眼,满世界都是你,那个倔强的,那个勇敢的,那个,啊,那个无法忘记的,背影! 我把刃拳码头改成了你的名字!刃拳?哼,卡加斯,这个,这个背叛者,请原谅,我只想得起这个词来形容他。我不是有意冒犯你,如果你此刻听得见的话!他臣服于伊利丹那个,精灵,而你服务于伟,大的部落!
我能感受到你当时的感觉,当时,面对巫妖王的时候,面对霜之哀伤的时候。那力量吞噬了你,你的灵魂,就连巫妖王自己也无法摆脱。我见识过比那还要古老的力量,还要强大的力量,我掌控了它!
哈,巫妖王!那些人类喜欢叫他阿尔萨斯(可我们从来没有叫过他耐奥祖),他们骨子里还有些许为他掩藏的骄傲。如果那样的话,我是说,如果像人类那样,我应该去敬重卡加斯,而不是你!
那怎么可能?
德拉诺什,噢,我的兄弟,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是人类,我是兽人,我是玛格汉!
玛格汉,看呐,我们都是玛格汉!阳光照在我们皮肤上的时候并不刺眼,就像大地和泥土那样宽厚。而那些野草,生长在大地之上的颜色,我接纳了他们。
玛格汉,啊,我怀念那段岁月,就像我怀念你一样,因为你们都死了!哦,不,你死了,玛格汉还在,纯血兽人还在,先祖的荣耀还在!但,但我感觉你又没有死!就像,就像此刻我觉得你就在这里,在这里听我对你说话!
你还记得吗?我们一起躲在帐篷里,还有约林,还有谁,记不得了。我们躲在那里,像三只塔布羊的雏崽,是的,甚至连狼崽都算不上。啊,我感觉我的牙齿在抗争,它打断了我的思绪,但是这让我又想起了当时的情况,是的,牙齿!
它刺入了我的嘴唇,现在那里还有痕迹,虽然很小,小到没人注意,但我记得,它就在我的鼻环旁边,你瞧!
我嘴角的肌肉在向上跳动,呵,我们跑题了,嗯,那时候,这些稚嫩的情绪,是向下的。不不,那不是哭,我怎么可能哭?对,我们都没有哭,我是咳嗽了,可那不代表什么,我当时……你可以去问问约林,他的记性最好,要不然就记不得那么复杂的恶魔符文了。恶魔,呸,我讨厌这个字眼,所以我也讨厌他! 他也讨厌我!
嘿,我不讨厌你!好吧,我以后不讨厌他了!唉,我做不到,我试了不止一次,你知道吗,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父亲,我们的父亲,变得,变得强大。而我们,却因为承受不起那种力量,躲在暗处瑟瑟发抖。 嫉妒?不,这不是嫉妒,是憎恨!恨,你懂吗?
看来我们还是有些不同,你从来没有这样的体验。是的,你也恨过自己,当暗血部族袭击日泉岗哨的时候,那时候约林正好跑来加拉达尔求助,我……是,是的,他自己解决了那些问题,可这也耽误了我的时间,不是吗?啊,再说,你不是也搞定那些破碎的杂种了吗?
听着,德拉诺什,不要再说以前了,这没有意义,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正憎恨着自己……
不用,不用了,兄弟,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道歉的。啊,可我还真的嫉妒过你,你们。是的,当你游历归来的时候,当约林重建血环废墟的时候,整个德拉诺都在传颂着你们的美名!

我的父亲……赞美?
不,我站在父亲的影子里长大,我知道我的影子也在里面,他也在里面!可就算我扔掉了血吼,他的影子还是挥之不去!
咳!
德拉诺什,你知道吗,我最嫉妒你的,就是你有一位无可挑剔的父亲,他几乎找不到缺点。
我记得,在战歌堡的时候,我第一次掌管力量的时候,我被你的父亲痛骂了一顿,啊,确实,不止一顿。你是怎么知道的?瓦罗克在儿子面前怎么这么八卦!嗯,八卦,这个词汇不错,我倒是要去问问那些熊猫人这到底什么意思,然后再回答你。啊,熊猫人?熊猫人就是长得像熊,但是头像猫的家伙!不不,不是熊怪!
如果我的父亲也能那样跟我八卦…….
对不起!我们过会儿再……好了,不要再提八卦了!
这不是八卦!
呼,对不起!
嘿,你在那边还好吗?你放心,我会让更多的人来陪你,朋友、战友,或许还有亲人,当然,更多的是,敌人!
没什么意思,我只是给瓦罗克写了一封信,派了最信任的人去送(反正她也是顺路),让他带着驻军赶回来,回来宰了那些联盟狗!啐!还有那些叛徒,异教徒!杂碎!
他应该快到了,可我觉得他只会独自一人!他舍不得你,你在那里!但他也舍不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为了部落,他会的……况且你现在在这里!
嘿嘿嘿!不要激动,我保证,我保证……我只是想念他了,想念我的了……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他,我就充满了力量。【一个迷途的女人】
啊,他恐怕是兽人最后的支柱,最后的信仰了!
不,不要提他!
没什么,我只是不想听到那个名字!
才不是呢!我是部落的酋长,我怎么会为一个女人生气?
我是玛格汉的酋长,在风之地的草原上,只有战歌氏族的女人才是最漂亮的!
你这是什么语气?德拉诺什,这个时候不要提扎伊拉,我不喜欢在背后说人坏话。没错!她喜欢龙胜过她
自己,她皮肤是黑了一点,她也不属于战歌氏族,可她衷心耿耿,而且英勇善战。她把龙喉氏族从莫什罗格那个混蛋酋长手里解放出来,从恶魔的手里解放出来,在我眼里,她比卡加斯都伟大得多!
你还说,那你怎么不提你邀请阿格拉狩猎被拒的事情呢?
嘿哈,别转移话题。唔,你怎么知道信使是她?
哦,是嘛,我有说过?
不,我刚刚说过,我信任他!
那是两回事!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疑了?我,我告诉了你!?怎么可能,什么时候?
不,你在撒谎!你在,你在这里,我在跟你说话,德拉诺什!我,我看得见你,你穿着萨鲁法尔大王的勇气战甲,持着高阶督军的战斧,你背后的阳光,你……啊……
德拉诺什,我的兄弟,我保证,我以酋长的名义发誓,我不会与他正面为敌!我不会……啊,我的头,好痛!

“他好像在喊什么?”【一个迷途的女人】
“把他的头盖好,别让他看到外面。他的脑子受过重创,意识完全混乱,说些疯言疯语也是正常的。” “是,掌门!”
“很好,船就要来了,耐心等候吧!哦,对了,季怎么样了?”
……
“怎么还没到,艾莎不是说联系上老伙计了吗?”
“我想,兴许是神真子体型太大了,移动起来也不方便;再者,这么个庞然大物,要是太快,恐怕整个码头都会被淹没的。”
“有理,那就再等等,正好太阳快下山了,不会惊动那么多人。”
“掌门,属下不明白,我们为何不直接乘坐天火号回去呢,或者,请大法师开个传送门?”
“这不是联盟,或者部落单方面的事情,这是大家的事情。你看看那些虎视眈眈的兽人,他们可没有这么容易承认自己的错误。加尔鲁什毁了这一切,可还有很多人认为他是英雄!所以我们要进行一场公正公开审判,把他的罪行公诸于众,这样才能让那些追随者从狂热当中真正和平下来。在这之前,我要保证他的安全!”
“你明白就好。对了,你倒是提醒我了,去把火金派的热气球开过来。艾莎要带季回迷踪岛,这艘最安全的海船正好载我们回去。可这第一步,我们得能够登上,甲板!”
“是,掌门!”
……
“他好像又开始了?他到底有没有昏迷?他一路上絮絮叨叨说个不停,可我听得出来,那不全是胡说。纳兹格林和他的切腹之匕,格罗玛什要塞的阴影,然后是,德拉诺什?啊,这里是德拉诺什尔封锁线,德拉诺什尔码头,噢!我明白了。”
唉,真是,真是太吵了!我都不能静下来单独和你谈谈,我们,就我们两个,就像小时候,我一个人,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你总会出现在我的身边。我记得你喂我卡拉果,当然是那种消化过的,哈,我当时竟没有认出来,我想我是太饿了。然后我追着你到处跑,你怎么跑得过我,要不也不会急得跳湖,然后,然后我们捉了很多鱼,很多很多鱼……
是啊,族里的大人都走了,我们眼睁睁的看着猎物却束手无策,甚至连塔布羊都来加拉达尔的窜门。哼!还有那些食人魔,他们占了我们的领地,没错,是嘲颅(废墟),他们还经常偷袭我们,抢夺我们仅剩的食物!
可我们,我们只敢躲在一起,那样他们还稍稍有些顾忌。可曾经,曾经我坐在父亲身前,驰骋在纳格兰的大地上,那些家伙只会远远的避开我们。父亲告诉我,他们不是惧怕我们,而是惧怕我们所掌握的力量!那些欺软怕硬的家伙,那些,呸,愚蠢的蛮物,我一开始就怀疑他们的忠诚。
啊,忠诚,只有我们兽人才是最忠诚的,最可靠的。我们流着同样的血,有着同样的信仰!是的,这是盖亚安祖母说的,我们敬爱的祖母。
我现在都还记得,她高高地站在加拉达尔的巨石阵中,她的声音,仿佛来自天空,让那个刚刚破碎的世界都欢欣鼓舞。她告诉我们,我们兽人,无论来自黑石、血环、战歌、霜狼,还是雷王、影月、刃拳、嘲颅、嚼骨......她把每个氏族的名字都高声念了出来,尽管我们世代分居各地,我们的口音也千差万别,我们的习俗也不尽相同,但我们都是兽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我们有着共同的祖先,我们流着相同的血,有着相同的信仰,我们一起驱逐食人魔,一起猎杀戈隆,我们是戈隆追猎者,是大地的子民,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我们需要团结,我们应该团结,就像我们祖先做的那样,团结成一个氏族!我们是,是玛格汉,血脉的继承者!你们有谁,会拒绝这样的荣耀?
为了玛格汉!
啊,那呐喊,此刻还让我热血沸腾。【一个迷途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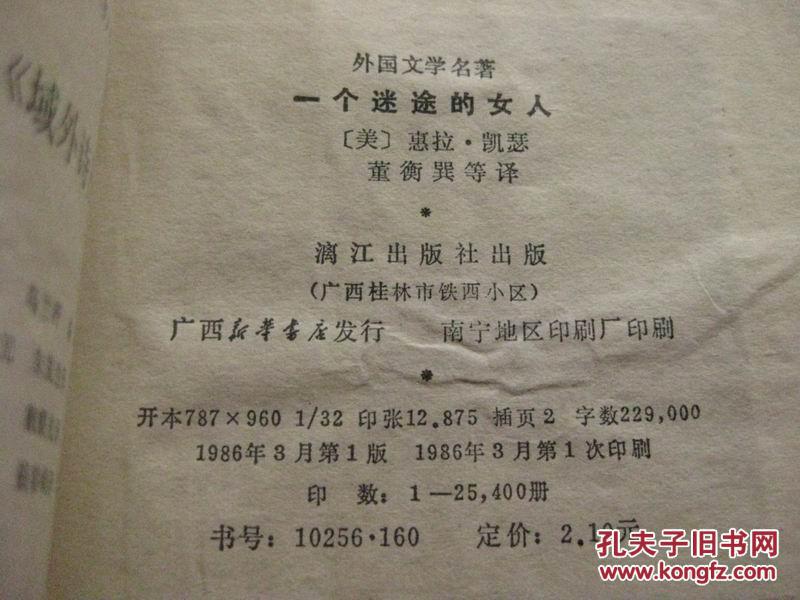
是的,我成了玛格汉的酋长,我原本以为祖母会让你来做,或者约林。可当她喊出我名字的时候,我知道,我无法拒绝。我第一次这样面对那么多面孔,那么多眼神,那么多……
不不,不是质疑,很复杂。我那个时候握紧拳头就像现在一样,我说,我是加尔鲁什,地狱咆哮,格罗姆的儿子。
我记得他们的表情,我咽了口唾沫,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看到你开心地朝我笑,可我就是说不出话来。如果是你,站在那儿,你会怎么说?
我是德拉诺什·萨鲁法尔,瓦雷克·萨鲁法尔大王的儿子。我是德拉诺之心,我站在这里,成为你们的领袖,玛格汉的领袖,我深以为荣……
呵呵,你后来就是拿这番话来数落我的。没错,我没有生气,从那一刻起,我知道,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自由的,肆无忌惮的计较,追逐!我是一个酋长!
于是我下了生平第一道命令,滚!
遵命,我的酋长!
你知道那不是命令,可你告诉我那是命令。从此以后我便开始指派任务,行驶酋长的权力,而只有你,才会听从。
祖母!祖母听从的是酋长的命令,她知道玛格汉需要什么,你知道的,那并没有多大的作用。
约林?他宁愿离开加拉达尔,也不肯面对我。他自以为很明智,在我看来那都是逃避,说到底就是不相信我,可他最终还是来找我了,哼!
是啊,加拉达尔稳固了起来,玛格汉也越来越强大,更多的人愿意听从我的命令。我小心地活在谦卑和谨慎当中,我生怕最后的希望在我这里掐断。每当议会在篝火前商议的时候,我总是很沉默。看着他们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羊毛兽皮的事都唠叨个不停,反复斟酌。我知道,他们还活在失落和恐惧中,而我和他们一样。他们最后会把目光转向我,无论出于什么目的。
就这样吧!我说。
我知道,我最大的敌人是我自己。
敌人,并不完全都是坏的存在。比如说卡扎克,如果不是他打开黑暗之门,伊利丹会掐灭最后这点星火。玛格汉要么毁灭,要么成为卡加斯那样的傀儡,而我,就是他们的酋长!我已经负担不起什么罪责了! 是的,我没有什么罪责,可我知道的太晚了,我本可以成为最有发言权的那个,最骄傲的那个,最荣耀的那个,一个真正的兽人酋长!昂首挺胸,一呼百应,驰骋沙场!我……啊……
你感受得到那股力量吗?那股埋藏了二十多年的力量,当他第一次在纳格兰响起的时候,我就知道,战歌永不陨落!
可惜你没有看到,德拉诺什,那一刻你没有看到,我多么希望找个人拥抱一下。不,他拥抱的不是我,而是他的老友,格罗姆,我感受得到。
我第一次感受到拥抱,真正的拥抱,兄弟的拥抱,是在北裂境。没错,就是和你告别的时候。我记得你和阿格玛大王站在一起,他那牛角头盔里喷出来的寒气可没有你的粗壮。你的父亲也在场,他亲手将战甲披在你的身上,并把奥金和鲜血打造的武器交给了你。
一个迷途的女人(二)
三环外:一个迷失的女人
那天我如常下班回家,走到小区门口,我和一个骑着三轮车收破烂的男人擦肩而过。我走了几步猛回头,眼睛定格在他的三轮车上。车里面放着很多杂物,最上边是一个鞋盒,我的心脏忽然停了一拍,那鞋盒分明就是我的。我以为家里遇贼了,可我明明记得我老公今天补休在家的。我慌张地拿出手机问他在哪里,他懒洋洋地说他搞了一会儿卫生,还把一些不要的旧东西扔掉了,现在刚刚上床打算歇一会儿。 我顾不得跟他细说,关掉手机马上就追了出去。三轮车踩得飞快,我一直追到离小区五六百米的天桥底下他才停了下来。那里有一间用破铁皮搭成的小屋,收破烂的男人正从车上往屋里面搬东西。我不敢太张扬,因为这是小区居民的必经之路,我怕遇到熟人。小屋里面乱七八糟地堆着很多东西,有报废的电饭锅、电视机等等,又脏又乱。我有些忐忑地问,大哥,你手上的那个鞋盒可不可以还给我?那是我老公扔错的。
这个个子很高但有点驼背的男人看了我一眼,我当时还穿着上班时的套裙,看起来就是个时尚丽人。他一定在怀疑,我这么漂亮的女人为什么会管他要回一个旧鞋盒。连我老公都不知道,我在鞋盒的一只鞋子里藏了四千美金,专门用一个信封装着卷在鞋子里。我此时也不好向他解释,否则更难拿回这笔钱。我平时是不大理会这种收破烂的人的,但当时我确实是低声下气了,我对他诌媚地笑,死死盯着那个鞋盒。
他眨眨眼睛,咧开满嘴的黄牙:我认得你,你是住在B幢的,你老公平时开一辆蓝色轿车,蛮嚣张的嘛。他突然醒悟似的自言自语:你这么有钱还紧张一个旧鞋盒,里面一定有好东西。我被他说中心事,脸一下子就白了。他更加得意起来,我要看看里面藏着什么宝贝?他将手伸进其中一只鞋子里摸了几下,摸出一个信封。他猥琐地看了我一眼,瞧,这铁定是哪个旧情人给你的情书,怕被你老公看到所以才藏到这里的吧。
我怕他会打开便焦急地想抢过来,但他啪一下就打掉了我的手:别动,动手打手动脚打脚。我不敢动了,他将我面前的一个易拉罐一脚踢到角落里:我知道女人都是养不熟的,我老婆就是嫌我穷才跟男人跑了。他鄙夷地看我一眼,你老公赚这么多你都不满足,还要去偷人,你这女人真贱!我心里很气,可我不敢驳他,怕他不高兴。
那笔钱其实也不是什么来路不明的钱,只是我结婚前和我老公有约定,两个人赚的钱都要存进联名户口。我老公对钱财一向都很小气,我妈平时就体弱多病,我想自己偷偷存点儿钱以防万一。要是这事给我老公知道了,他肯定会很生气,甚至可能会怀疑我不知背着他偷藏了多少钱。夫妻间一旦失去了信任,是很难生活在一起的。这个道理我当然明白,所以在这个满身散发着汗臭味的男人面前我一直忍气吞声。
他见我不说话,以为我心虚,马上就转移话题称赞我漂亮,还说我们小区里长得最有看头的女人就是我。他不怀好意地吸了吸鼻子,斜着眼睛壮着胆子说了句:你让我摸一下,我就还给你。他色迷迷的眼神让我很反感,可我偏偏不能得罪他。我想了想后果,知道别无他法,就铁青着脸艰难地憋出一句:你记得要说话算数。
他点了一下头,迫不及待地就伸手摸了一下我的胸部。我一阵反胃,他涎着口水说,真滑,然后他的手就伸了进去,同时身体还贴了过来。我害怕极了下意识地躲开他,捡起地上的鞋盒便往外跑,他想拦住我,我使出全身力气推开他。他脚下踩到一个什么东西就向后仰去,后脑勺碰到了角落里的一个破电视机上,血一下子冒出来,溅得电视机都红了。我疯一样跑了出去,不敢回头。
我回到家越想越害怕,我怕他会流血过多死掉,那样我就成了杀人凶手。正当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的时候,门铃响了。我打了个激灵,条件反射地躲到了洗手间里。我听到对话,是送快递的小弟,我长长地松了口气。那个男人一直没有再出现,那笔钱也很快被我处理掉了。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天桥底下,只是每次我看见天桥,都宁愿绕路也不愿经过。我一看见那个铁皮屋,就会想起那笔见不得光的交易,我会觉得自己很脏。
那年我十八岁,在广州一家夜总会里做服务员。那一天与往日并无不同,夜幕降临后,夜总会开始陆续有客人光顾。但不知怎么的,那一晚我却出事了。我将一个客人点的一瓶XO送进包房后,不小心滑了一下,瓶子摔在了地上,洋酒的芳香碎了一地。我当场就吓呆了,这瓶洋酒的进货价我晓得,就算我把做了半年服务员存下的钱都贴进去也不够赔。
我手忙脚乱地将碎片收拾好,拿来抹布抹干地板。刚好客人就进来了,他闻到酒香,以为我趁他不在私自开了洋酒,他很不客气地问我,酒呢?我怕他闹起来惊动经理,惊慌之下我马上去柜台重新给他领了一瓶洋酒,但领洋酒的单子,我却偷偷撕掉了。事后我越想越害怕,这是最低级的手段,只要客人买单,一切都会穿帮的,到时我不但要被客人追究,很有可以还会坐牢。
但是让人出乎意料的是,那晚发生了一件比我打烂洋酒更震撼的一件事。凌晨一点多的时候,夜总会里的陪唱小姐古兰披头散发地从一个包厢里冲出来。她语无伦次地指着包厢里一个醉醺醺的男人对经理说,她被他强奸了。当时她的样子真的很可怜,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经理不相信,在这个地方男女之间通常都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经理说你有手有脚,你不会跑吗?
古兰争辩说当客人非礼她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就是跑,但不知为什么包厢的门却被人从外面锁上了。这个理由让所有人都觉得好笑,从来夜总会里包厢的门都是不上锁的。最重要的是在这种醉生梦死的地方做事的女人能贞洁到哪里去?古兰喊强奸,根本没有人信,甚至有人怀疑是不是她和客人谈不妥条件,或者最后客人给的钱不够多,所以她才翻了脸。
古兰却不肯罢休,她报了警。警察很快就封锁了现场,那个仍然迷迷糊糊的男人被抓了出来审问。因为警察的光临,夜总会一下子就乱了起来,鸡飞狗跳的。这件事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根本就没有人理会那瓶不翼而飞的洋酒。因为没有证据证明那个客人使用了非常手段强奸了古兰,客人被放走了,只剩下古兰一个人很难过地坐在夜总会大厅的沙发里哭。
没有人理她,她已经成了众矢之的。她破坏了夜总会的生意和名声,甚至差一点打碎六十几个人的饭碗,没有人再欢迎她留下来。惟独我走近她,递给了她一杯白开水。她感激涕零地向我点点头,哑声说,谢谢你。我避开她的视线,不敢与她对望。我说其实我应该向你说对不起,因为是我将你介绍给那个客人的。她摇摇头,她说不关你的事,是我自己运气不好。
她黑白分明的双眸分明对我没有半分抱怨,可是我心里却不能原谅自己。其实我知道她是一个规矩的女孩,她在夜总会里陪唱,但从来不陪睡。她和我一样都是打算在这座城市里栖身的女孩,不想弄脏自己。是我,我明知那个客人喝醉了,他进包厢的时候私底下还叮嘱我,替他找一个放得开的陪唱女。于是我就将古兰介绍给了他,在古兰进去之后,我偷偷拿出备用的钥匙,将门从外面锁上了。
我记得小时候我很调皮,经常做错事,每次都让父亲打个半死。直到有一次,我和同学打架,新衣服被撕破,我已经做好了被父亲打的准备。可是那天父亲根本没理会我,因为我十八岁的姐姐竟然夜不归宿。父亲为了审问姐姐,根本顾不上罚我,我因此逃过了一劫。从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当用一个大的错误去掩盖一个小的错误时,那个小错误就会显得微不足道甚至不为人注意。
为了掩盖那瓶洋酒被打破的事实,我才锁住了包厢的门。我之所以选择古兰,就是因为我知道她不会顺从,只有当她把事情越弄越大的时候,我才会被所有人忽略。那个时候我自顾不暇,所以没想过这样做会伤害到谁。直到第二天古兰在夜总会里销声匿迹了,我才意识到我的自私。若非伤心欲绝,谁都不会轻易离开这座人人向往的城市,我不会,古兰也不会。
许多年过去了,我却仍然不能忘记那一晚。我想,或许只有某一天,当我知道被我伤害的那个女孩仍然幸福的时候,我才能安享生活。
http://m.zhuodaoren.com/tuijian354124/
推荐访问:一个女人的史诗 忏悔录迷途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