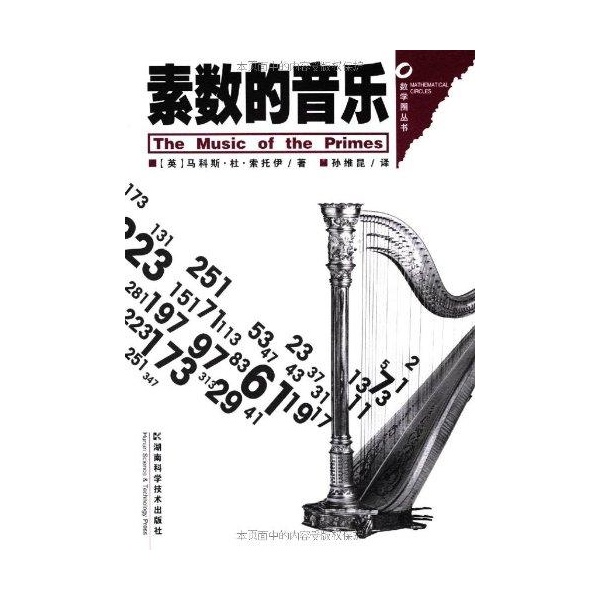在邯郸西部山区那个叫做北贾璧的村子里,(一)
邢台大贤村:洪水里的生死场
【在邯郸西部山区那个叫做北贾璧的村子里,】 脆弱的村庄,脆弱的生命。 这个周末,河北邢台的暴雨遇难统计经历了一次戏剧性的翻转。在7月19日“20年一遇”的暴雨之后,石家庄、邯郸皆频频告急,但处在两者之间的小小地级市邢台却一度失去声音。20日下午,邢台经济开发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受灾民众一直在转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这个平和的说法在22日被打破。
当天,该区东汪镇、王快镇的村民来到107国道上,甚至“抬上尸体”拥堵在邢临出口上,抗议政府不上报。正巧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王清飞前去指挥救灾工作,双方僵持之下出现了媒体报道中的“互跪”一幕。
邢台的遇难人数从那天起开始滚动,从25人遇难、13人失踪,到本刊发稿前为34人遇难、13人失踪。在官方名单里,开发区17人遇难,1人失踪,而东汪镇大贤村可谓是重灾区,8死1失踪。在有关洪水的天灾人祸里,邢台的案例是并无新奇的一个常规性灾难,因为多数天灾里都可见未防范和不作为的影子,而多数人祸都会在某个近乎天意的时刻一触即发,这似乎已成规律。
失踪的女孩
19日的大贤村,下了一天的暴雨,这对于村南头“桥东板厂”的张苏辉一家是极其无所事事的,他和妻子李小慧(化名)、4岁的女儿张梓阳在南屋待了一天。他还有个9岁的儿子,在村里跟着母亲住在祖屋,本来女儿也是由母亲带的,毕竟夫妻俩住的是板厂。平时在那儿监工、料理厂房,但下雨开不了工,夫妻俩就把女儿带回身边,好让母亲休息一下。
19点吃饭的时候,院子里的水已经漫过脚踝,他们用水泵给抽走了。这个三亩地广的厂子正处于洼地,雨水可以四面来聚,顺着下斜的路阶流向那半地下式的院 子。21点30分的时候,正常来说该入睡了,夫妻俩冒雨冲出去,把停在低洼地的本田车开到高台上,回来掩上大铁门逃进屋子。这扇没有关紧的大铁门似乎已预示着一个魂飞魄散的雨夜。
李小慧在22点多就昏昏欲睡了,女儿还在床上看电视,看着看着习惯性脱掉单衣,光着身子睡着了。张苏辉一个人睡在前厅“守厂”,外面就是半敞露式的厂区,雨水沿着棚沿浸过仓库里成谷堆的胶合板。那个晚上有诸多异样让他觉得不放心,他知道整晚有暴雨。
凌晨2点,李小慧被弄惊醒:“洪水来了,赶紧走。”其实那时候内屋还没进水,她抱着赤裸的孩子惊慌中走到厅里,发现家里已经停电,她已忘记夫妻俩是谁开了那道单薄的铝合金的厅门,但他们看不见,外院的洪魔已有2米多高。水是闪电般把人吞噬的,先把她和孩子甩进厅里,失手冲散,再双双被裹挟出门框。她记得在水里跟丈夫最后说的一句话:“我抓不住她”,“我也抓不住”……两个人扑棱到屋外,在裸砖累累的屋檐下有一个铁把手,那是几年前张苏辉为挂鸟笼子特意插上的,他先把妻子托上去,再攀过空调管子上了房顶……接着,是如同在一片漆黑海面的岛屿上度过生命中最长的5个小时,没有手机和衣服,徒手站在夜雨里,劫后余生的滋味里让他俩根本不知道那被冲散的女儿意味着什么。
23日,事过第4天,邢台的伏天蒸湿难耐,太阳的热度在水汽里湿烤着受灾后狼藉一片的村庄。不宽的主路上是一片泥国,洪水虽已退去,但整个村庄都是淤泥,耕地尽被褐土覆盖。洪水过后,家什、货堆、庄稼等都已改变了格局。
张苏辉拄着根木棒在主路上无力地蹒跚着,路上的垃圾、淤泥更是拖慢了他的脚,村民向我指指他,他4岁的女儿张梓阳还没有被找到。在当时,村里已确认8例死亡,1例失踪。前一天上国道堵路“互跪”的几名村民中,其中有一个就是他的母亲,孩子的奶奶,她跪下求告王清飞自己的孙女仍未被找到,对方也无奈地跪下称一定会帮她。于是在翌日一早6点,公安、消防队拉成的“官方救援队”开着铲车来到他家里和他的板厂。
一个五大三粗的35岁壮年男子,眼皮红肿着,带着朋友和亲戚已经在村里扒拉了4天,他明显是眼泪哭竭的样子,喘着大气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沿路的人都同情地招呼着他。所有土地上的物什仿佛都已挪动位移,但都覆盖在或浅或深的淤泥下看不见,张苏辉在村南和村北间一遍遍地找,他趟过玉米地,用木棒翻搅着歪进泥里的玉米梗,地里非常不好走,深一脚浅一脚。
“她是光着身子被冲走的。”24岁的李小慧说到这一句时脸又抽搐起来,她在自家的厂子里扒着,觉得孩子应该还在后厂里,在山垛般的烂木碎屑底下。如今,屋里是一片泽地,所有的家具都错了位,如同泥里活脱出来的文物,墙壁上的水线超过2米。“我已经哭都哭不出来了。”她眼角泛泪,但忍着不掉出来,戴着塑胶手套,在废墟里跟我说,伏天让她的脸涨得通红。
如今,她家是村里唯一的救援现场,铲车开进惨不忍睹的厂房,在每一片区域把遭水浸泡的胶合板一茬茬地翻起,一名监工的开发区公安民警告诉我,“反正这厂子必须得清干净,没有的话再慢慢往外围拓展”。那位监工用背水一战的决心说着,一个个接着上级的电话,确认孩子还没有找到,但是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找到孩子。
由于厂前的S326省道正在修热力管道,整条路被挖得一片狼藉,铲车开进板厂并不容易,必须把路上的挖坑填满才能开进去,所以23日那一天的效率并不高。但要好过前两天,在救援队、挖掘机还未进村的时候,村民只是松散地跟着消防队自发救援,就那样发现了那些泥地里、挂在障碍物上的遗体,整个村子如同一个痛苦无告的孤岛。
张苏辉的厂几乎是出了村的南头,壮观的京广高铁线从他家边穿过,架在邢台的母亲河七里河上,东边一里地就来到河道上的大贤桥,村里土名为龙王庙桥。自1996年8月洪水以来没有再泛水过,但20年后的今天,龙王庙镇水的神话想象仍无法阻挡西面而来的山洪,毋庸置疑,张家是洪水进村的地方,而特殊的低地让他首当其冲。 大贤村在22日午夜举国皆知,在村民的描述里,如果不是去国道上一闹,现在的邢台就淹没在石家庄、邯郸两边的消息里了。因为南边紧挨着七里河,也使它的经济与生命损失比镇上别的村来得严重。
洪水卷过的村庄
这个村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有着做木板生意的渊源,在基础建设刚刚兴起的那会儿,这里的大厂子动辄一个月流水就几十万元,跟一般的空心村不同,这里并不兴外出打工。张苏辉的厂子中等规模,1996年就建成了,业绩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几万元,如今经济不景气,也就勉强度个小康的生活。无论如何,在洪水前他是一个殷实的个体户,跟他一起找孩子的一个中学同学痛惜地告诉我:“本来我们同学中属他最好,现在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村里开板厂的比比皆是,但无一不倾家荡产。因为已是第4天,那些投奔亲戚的村民陆续从镇上回到家中探视,死闷的村里才有了人气。我在镇上从北向南地进村,一路经过东静庵、王麻村,最终到大贤村,灾情越往南越严重。各家在颓垣断壁前拎着水桶找水,或无所事事地聚集伫立,看哪家的损失更严重。面对毁坏的房屋和庄稼,他们束手无策,很多院子都晾晒着霉臭的棉被,是褐色的田地上不多的色彩。
村北的张龙飞也回来了,坐在四合院的门前,至今惊魂未定,说起来就激动万分。他穿着一身别人给的衣服,皮带还是女式的,一站就得束一束快掉下来的裤子。“我连衣服都是别人的,什么都带不出来。”他自己也笑了。
他把洪水中激荡出屋子的家具一一排放在院子里,拖出棉被搁在院子里晾晒,但横竖都是脏的。他发现,除了把倒下的家具扶扶正,什么都不能做,洗衣机、空调耷拉在院墙下,“东房的冰柜不知道怎的冲到了南棚了”。无聊中等来一拨拨儿记者,在他堆满破家具的院子里拍照,看得出来他所有的财产都曾经如浮桴般漂着。“怎么拍都可以,我现在有得是时间。”他说。
那天凌晨,水几乎是同时到村南村北的,张龙飞家的水是从村西的农田翻滚而来的。2点不到,他在睡梦中接到一个电话“快醒醒,发大水啦”。这时,床下的水已经漫过脚踝,他走到院子里就发现不对了。院南的板厂里还拴着条狗,“我想着还要去救我的狗呢”。他义无反顾跳到齐腰深的水里,摸索到了厂子。厂里的水已如同一个泳池,货物浮在水上,狗浮在笼子里,他救起狗就立马把其余4口人弄上了房顶,一家子在凄风苦雨的房顶上等了一宿。
“当时还下着雨,刮着风,雨量应该在大雨到暴雨,我们在房上顶着雨,吓得啥都听不见看不见,我的后边就是一片海。”在房顶上,他手里还捏着个电话,但这时的信号已“一片盲区”了。直到20日早上9点,雨还在下,见水稍微退了,一家人才试着下房顶,走到北边的村卫生院,一路上“根本就没有见到有政府部门的人”。在医院里等到中午,村后街一半的村民已经会聚到卫生院了,武警过来了,把他们撤到了村南。
“这就是我的厂子,来看看这个效果。”他把我领进厂房的时候,满目废墟,他说他什么财产都没有了。说到经济损失,他说“有50万”。北屋的房间几乎已空,只留下墙上一张婚纱照,地上还有泥泞。张龙飞已经住到亲戚家,除此之外,镇上还有三处政府安置点,无亲无靠的人可以去那儿登记。
那天,官方组织的重型机械还无法进村,只有零散的人工在清淤,对于北边还有一大片的村子来说,挖掘的力量就明显不足了。“我们这里人手有限,”上述那位开发区民警对我说,“现在只能先救援,以后的事再慢慢推进。”确如很多村民都认为的那样,雨可能还会下,洪水可能还会来,村里还面临不确定性,要把整个村掀个底朝天。有些事现在肯定推进不了,但是着急的村民还是不解:“你看一天了,这村里有见到警察和消防队的车吗?”一个坐在京广线下的桥墩上的大爷对我抱怨着,他说那几天他没有见到任何村镇干部的人影。
“绝对没有泄洪的通知”
24日21点,当我在村卫生院的大楼前见到村支书张战歌、村长高永忠的时候,他俩正一个嘶哑着嗓子跟村民交涉,一个坐在地上吸着烟。卫生院三层楼高的北楼已经安置满了灾民,一位无亲无靠却又不愿出村安置的妇女无论如何也想带着孩子住在院里。“我跟她说已经没房间了,有房间会不安置吗?”高永忠说。北楼所有的病房都挤着2到4个人,他们男女分开地住着,一到了晚上,这是村中唯一热闹而充满人气的地方,灾民就着矿泉水和盒饭在院前的救灾伞下摆着龙门阵。
4个晚上,张战歌几乎没合眼。“拿一块纸板铺在地上打会儿盹。”他坐在花坛沿上吸烟,无力地向我指指墙角。19日那个白天,他在自发的微信群“美好大贤”里跟村民的对话被贴到了网上。那天上午10点半,他在一个129人的群里说:“我们一直在关注汛情,大家不要惊慌,如有危险会及时通报。”有人还在群里说:“发不了山水,这点小雨。”只是在翌日凌晨1点51分,一串发自镇防汛办高姓工作人员的消息打破了一切平静:“七里河放水,现在正放着,叫都往大贤桥赶。”他后来在群里感叹:1点47分接的电话,1点51分发到群里,2点还联系不到熟睡的家人……
那个晚上,张战歌为可能来到的汛情值了班,23点时他和高永忠开着卡车来到大贤桥上,暴雨夜里只能躲在车里聊聊天,抽抽烟。但是,他坚定地跟我说,那个白天是有强降雨的通知,“但绝对没有泄洪的通知”。“我们都是镇上的‘包村干部’通知干啥才干啥的。”他自己是一个村化工厂的老板,当上支书才两年。
1点50分,值班近3个小时,他的手机响了,通知七里河的水要来了,赶紧撤离村民。他走下卡车来到桥墩上,雨帘中望着西宽东窄的河面。“大概几分钟后,突然听到一阵声音。”那时洪水排山倒海地朝桥口冲来,他比画了下,水冲到桥体上是1米高的位置,那时他的车就在往村里赶,而洪水就在后面追来。“只要晚半分钟,我这车就被顺走了。” 张战歌脑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村广播站喊喇叭,喊了六七分钟,就看着水从腿肚上涨到腰上,直到一楼广播站的话筒被水淹没。他慢慢地和高永忠拉着手走出去,用手机一个个电话打出去,包括“119”、乡政府,“但是他们也进不来”。他们爬到大院外的一个戏台上,渐渐信号全无,等到4点左右天边熹微,他们下了水,拄着棍子在村里�水。“主要是绕着走一圈,互相喊一喊有没有人。”这时在水里跟一些水中的村民接了头,一起往楼高的建筑走。那天直到中午,才把村里2000人都撤走。由于没有信号,那天下午才有人来报信,他家中妻小都没事。
“救援应该是第二天才开始的,第一天是大面积撤离,救援时间被耽搁了可能也是有的。”这位36岁的村支书说。他曾经对媒体讲过一句话:“700多户,2000多人,不管你有多少钱,一夜之间大家都成了光头。”现在他已惊魂初定,拖着疲惫的身子在卫生站的大院里找板床或墙角靠一靠,低沉着沙哑的嗓子缓慢地跟我说:“那天晚上22点是接到镇汛情办的电话,说今晚要值班,我还顺便问了问河会不会放水,他说没接到通知。”
22日前,网上的邢台救灾一片安宁有序,只是当晚一条爆发的消息称,“水库泄洪,未通知大贤村村民”,才让一切曝光。即使在与外隔绝的头一天,村民都不信这是自然暴雨造成的水,在他们的口口相传里,那晚街面上的水有的可达2米高。
根据后来官方发布的信息称,造成东汪镇灾情的洪水,来自于七里河上游的东川口水库漫溢出库的水,与西部山区汇入南水北调西侧的排水沟的水流,两路来水汇合成大水。东川口水库是敞露式的溢流坝,雨水接近坝顶时会自动溢出。
七里河是邢台的一条行洪河道,从西边天梯山处的东川口水库开始,七里河一直延伸到市东经济开发区,是一段32公里的路程。从地图上看,自西向东的河道在东汪镇处突然收窄,并微微向东北拱起,往村里的部分就被叫“顺水河”。可以预见,水势是从西南方向往东北裹挟的,对于村北的房屋,它几乎可被西面的来水直接裹挟
根据之后媒体报道,两路洪水汇合达到580立方米/秒,仅东川口水库的泄洪量就在382立方米/秒,而七里河上大贤桥段的设计泄洪能力为150立方米/秒,是“河道易出险部位”。但一个人为的隐患却在今年春天埋下,S326省道由于修热力管道,导致垃圾都往桥下填埋,如今的桥西,可见废砖砂石把河道收高,桥洞前一摊死水的样子。一位村民对我解释,原来宽阔的水岸边是有防汛墙的,今年5月垃圾一来破坏了百来米。
官方后来称,当时桥下的通过能力只有40立方米/秒。张战歌后来对媒体讲,希望能尽快修整河道,加固加宽河坝,“把桥的朝向改一改,让七里河水不至于在这里遇到拐弯直接冲击河堤”。
那夜在水库边
从邢台县县西的天梯山风景区到东川口水库还有七里远,从西黄村镇进去,经过南会村,就是绵延不尽的山区。伏天的山里云蒸雾罩,有耕地处尽是一片被水冲毁的平芜,齐肩的“青纱帐”自西向东倒去,但是南会村的村民在敷了沙的路上忙着“自救”,他们根本顾不上庄稼。洪水过后第5天,村里的拖拉机络绎不绝,然后再往山区挺进,就可见路毁桥断,那条唯一通向水库的路原本可通车,如今只能步行。
越是往山里走,救援力量和物资越不达,一路上,朱庄村、寺北坡村越发阒寂,倾圮的房基越多,无所事事的村民坐在倒下的树干和桥墩上闲聊。寺北坡村的田军明在镇上开了一个通信店,移动公司发来免费的通话卡,但这里的信号时断时续,他认为也没什么用。他家所在的寺北坡村是通向水库的最后一站,房子盖在半山坡上,他家当晚被埋在泥石流里,“泥水盖过了房顶”,所幸这个村比较好的是,当晚九十点钟就通知了,山腰上的村民都撤了。
至今被困在东川口水库坝下的王文龙5天来只出过一次村,走了一个小时的山路去镇上买水泵,跑了4个店面才买到。“因为什么?家家户户都买水泵,买不到了。”他向我描述这55年生命中最具戏剧性的这几天,用三段式描述就是:“吓得半死,冻得半死,饿得半死。”他是东川口水库水电站的站长,干了26年了,还是编制外的,但他是“离灾情最近的那个人”。他说:“我既是经历者,又是旁观者、帮忙者。”
19日那个白天,雨一直下,到了20点后,越下越大。“乡镇领导就在村里住着,22点还过来巡逻,叫我把守好岗位。”他所在的位置是县水利局水库管理处宿舍,山脚下一幢很不起眼的两层楼房子,楼下就是水库发电机机房,比他所在位置高一点的山体上是没有挂牌的管理处办公楼,这里的一切都让人难以发现。
东川口水库库容是280万立方米左右,按邢台小Ⅰ型水库2016年的调度计划,当这个水库的汛期限制水位是224.3米,超过这个水线就得人工泄洪。在《邢台市小I型水库2016年汛期调度运用计划表》中可见,东川口水库在水位超223.5米时,实行输水洞泄洪;水位超224.3米时,输水洞与溢洪道共同泄洪。
所以,该水库虽然为自然溢流型,但在王文龙的水电站边有个泄洪道,可人工进行“输水洞泄洪”。“但那个设计能力太小,10个流量(立方米/秒)都不到,根本不起作用。”他说。22点,他帮助管理处的人员打开水闸,“也就1到3个流量左右”。他坚称,七里河决堤的水就是溢坝的山洪,跟之前微乎其微的人工泄洪无关。
他描述了那库水涨时惊心动魄的细节:“22点前,那水还涨得很慢,一个小时5厘米左右,就在22点后,一个小时涨了30厘米。”这个水库的观测是肉眼观测水位标尺的,一个小时一次,坝边还有个管理处的观测房,3个人值班。王文龙零点下楼时,是因为断电了,他去发电房里一看,水已经有1米深,那时发现不好了。他来到室外,漆黑一片,水已漫过七里河上游的河道,没了脚踝,他下意识地感到,这个水要比“96・8”时大,因为当时他也在这个位置,水并没有漫上堤坝。 之后的一切更像场梦。“我用手电筒往西边坝下照的时候,确实看不清什么,只有一股白烟,没过了桃树林,后来想想,其实是水汽。”他迅速把车推到高处,一个劲地往山顶观测房跑,那时的他只穿着一条三角裤衩,身后的洪水向山下泄去,已分不清河道与山路,那情形就像在瀑布边上逃生。
1点左右,他上了观测房。两个手机的联通和移动信号都已中断,他与3个值班人员拉响了警报。“确实是拉了,拉了4次,靠手摇的,但是水声太大,根本听不见啊。”他说。在那种情形下,再凭手电去坝上看水位也是不可能的了,事后,他们再上坝顶,看到那留下的水线比224.3米的出库位置高了4.5厘米。按照后来邢台市水利局的通报,20日凌晨2时,东川口水库水位达226.6米,水库蓄水445万立方米,已经超出其调节库容143万立方米。
现在再回忆,他认为整个下游的损失本可预防,因为水从西到东还要流经30多公里。原因就在于“通讯中断,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系”,活活耽搁了通知的时间。“如果当时有卫星电话、无线电,就不可能夺掉那么多人的生命。”看了26年水库,当了24年站长的王文龙叹息着,“我们这里级别太低,投资力度太小。”
这个水库的建造史要回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是苏联专家设计的,山下很多村民中的老一辈还上山修建过,他们回忆,当时就是把山石爆破,在库前用钢筋水泥一浇就成了坝。1963年8月,邢台也遭遇了特大暴雨,大坝被山洪冲垮,坝石滚落村里,之后就经历了一次新建,维持至今。水库管理处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有了1963年的教训后,为了减少库容,不再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就把新坝放低了5米左右。”
回想60年代雨水还充沛时,水库设计了人工泄洪道,一方面也用作灌溉。“以前水库受灾时,那水都给免费使用,现在干旱了,水利局不肯给你放水,灌溉都得买水厂的。”田会明说。当地的雨水就是这样,要么连年河道干涸,要么就像这次20年一遇。
7月24日,县水利局、水电厂的领导进山来看望了一次王文龙,见他买了个水泵,鼓励他做好自救工作,还给了他1000块钱。“但现在拿了钱也花不出去。”他对我说,现在的寺北坡村人迹罕至,物资难达,他口粮都不够。因为桥断了无法回家,索性看守岗位,“等发电机烘干起码也要半个月”。
艰难的善后
7月23日晚,邢台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市长董晓宇率领一众市政领导在发布会上鞠躬道歉。他检讨道:“首先,政府对这次短时强降雨强度之大,来势之猛,预判不足。其次,由于多年来未发生大的洪灾,各级干部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的应急能力不足。第三,灾情统计、核实、上报不准确、不及时。”
7月24日,河北省委通报,将对此次防汛救灾中工作不力的邢台市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段小勇,经济开发区东汪镇党委书记张国伟,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何占魁,井陉县副县长贾彦廷,做出停职检查的决定。
1996年8月的特大洪水是继1963年来的第二次,为了吸取教训,该市在2006年决定疏通改造七里河。但目前,从龙王庙桥上向西眺望,并没有规划里所涉及的“绿化公园、滨河景观带”等,而这座土桥因为被洪水猛冲而一片狼藉。一位村民说:“原来在造京广高铁线的时候做河堤硬化,把高架下的一处河坝拆了,现在也没有再造上。”据其他媒体引述官方说法,整治工程仅限于河流中断,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邢台市区。
七里河是子牙河水系滏阳河的一条支流,而子牙河又是海河的五大支流之一。七里河全长100公里,在市区穿过的那一段风景优美,而延伸到县区的两头就黯淡了许多。自2006年起,邢台市采用地产开发回补建设资金的方式,开发了七里河清淤拓宽整治工程,在当时的实施意见中,写着:“七里河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理,严重影响了防汛泄洪,使邢台城市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胁。”
工程在2007年时已累计完成投资10.8亿元,“经初步测算,整个工程将投入70多亿元,在治理19公里河道的同时,整理出城市市政建设用地近18平方公里。到2020年,将形成一个面积近60平方公里的七里河新区,相当于又崛起了一个新邢台”。时任邢台市委书记董经纬在一篇文章里如此表述。邢台市的目标是,要让七里河形成“防洪行道”,使防洪标准由不足5年达到50年一遇。
24日的19点,在还未暗下的天色下,龙王庙桥附近水泄不通,各种清渣、清障、挖掘机、铲车或拖拉机都开上桥墩会聚,一个物资救灾点就在滚滚的车轮和黄土边,地上堆满矿泉水和衣物。有的车贴上单位的红色横幅开来开去。“今天所有的单位都来了。”一位城管局垃圾管理处穿着制服的人员说。前一天,大铲车还进不了村,但那天的村里主干道的淤泥已经被清理。
张苏辉的“桥东板厂”已经基本被翻了个底朝天,厂里的碎木屑如今都堆在公路边,但就是没有找到孩子。8点时,他的姐姐张苏霞独自坐在一根轮轴上,此时的铲车已经撤离。“他们看我没有走,都不好意思撤,我说你们走吧。”她一脸疲惫地告诉我张苏辉夫妇已经回家休息,“不然还能怎么办”。但是她说:“明天等到这厂子的边边角角都清干净了,就要向外围扩了。”
天渐渐暗尽,京广高铁笔直地伸进黑压压一片的村里。我从村北再次进村的时候,在卫生院碰到了张战歌。将近5天,他没有回过自己的屋子看一眼,直到7月24日下午,他才见到了孩子。每个通宵,他和高永忠安排人员去村里巡逻,防止“趁火打劫”。说到为什么村民找不到他,他说:“受灾点太多了,实在忙不过来。”
目前,卫生院的救灾物资仍然短缺,但他认为要尽量自救,不要过多给政府增添麻烦,因为还有别的受灾点。夜幕中,他找到了一张扔在外面的病床,无力地躺在上面,一个个地接着电话。“政府安排了20个电工过来抢修照明,但今晚材料运不过来,只能等明天了。”

http://m.zhuodaoren.com/shenghuo334971/
推荐访问:村子里的英雄 村子里的泉水